《家在世界的屋宇下:諾貝爾獎經濟學大師阿馬蒂亞.沈恩回憶錄(Home In The World: A Memoir)》,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沈恩(Amartya Sen, 1933-)的回憶錄,他獲獎原因是為「感謝他對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的貢獻」,不過他的成就不僅是經濟學,還有對社會、人性的關懷。
序言中他提到了伊朗數學家阿爾─畢魯尼(Al-Biruni, 973-1048)在《印度史》中說:「印度人的數學非常好,但是印度學者最了不起的才能卻是另一點:他們總是能夠把自己一無所知的東西說得天花亂墜」,沈恩認為:「如果我也是這樣,那我會對自己這種才能感到自豪嗎?我不知道,但是說不定我應該從只說自己確實知道的事情開始。這本回憶錄就是這份努力的小小嘗試,無論我談的這些事我自己是不是真的知道,但至少總是我的親身經歷」。
本書紀錄了他的童年、學思歷程和研究生涯,人生足跡遍佈於今日的孟加拉、緬甸、印度、英國和美國,「處處是家鄉」是他對這些經歷最佳的註解。
沈恩的童年和泰戈爾
沈恩的外公克西提.莫罕(Kshiti Mohan Sen,註:沈恩母親娘家姓氏也是Sen)是著名的印度梵文和印度哲學學者,他「不僅拓寬了泰戈爾自己對古文經典的理解,甚至還擴及對民間信仰,更重要的是對民間詩歌的認識」,這類似於所謂的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任教於現在屬於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桑蒂尼蓋登(Santiniketan),一所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5)於1901年創辦的學校「維斯瓦巴拉蒂(Visva-Bharati)」,即是以學校所傳授的智慧(Bharati)來成就世界(Visva)(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5)。
克西提.莫罕與泰戈爾——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二首詩作被印度和孟加拉作為國歌——有著深厚的情誼,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代泰戈爾訪華、赴日時,他也陪同訪問。
因為母親家族與泰戈爾淵源頗深,沈恩媽媽Amita也在泰戈爾的學校接受教育,後來成為劇場舞者,跳的是一種泰戈爾開創的新式舞蹈,也擔任過好幾齣泰戈爾歌舞劇的女主角。這個職業選擇在當時中產階級出身的而言,可說是非常前衛呢!
他的名字Amartya也是來自於泰戈爾的建議,這個在梵文中指的是不朽,還有字面上代表靈異的意思。不過,他的錫度表叔,當時因為意圖顛覆大英帝國而於監獄服刑中,「老是抱怨阿瑪蒂亞這名字太難念了,說怎麼會給小孩取這麼詰屈聱牙的名字,顯然是泰戈爾開始老番顛了」。
沈恩的祖父是法官,父親當時是達卡大學的化學教授,所以幼時的生活主要在達卡(現在孟加拉的首都)、他的出生地和外祖父母所在的桑蒂尼蓋登。不過他最初的記憶卻是從加爾各答航向仰光的船隻汽笛聲,當時他的父親是受邀赴曼德勒任三年的客座教授,所以他幼時最鮮明的回憶,便是迷人的緬甸:「緬甸有著無窮無盡的美妙體驗與風光美景,這正是世界展現給我的真實樣貌」。
不僅如此,緬甸女人的強勢、掌握經濟活動和家中大權的角色,也成為沈恩的重要緬甸印象,「或許還影響了我對於性別議題的態度,幫助我思考女性的能動性(agency),成為我後來研究主題之一」。
這個關於緬甸性別的觀察,讓我想起自己的緬甸印象,數年前造訪緬甸時,對於仰光街頭的商店主和街頭群聚,都是以男性為主的情況印象深刻,本來以為這大概就是男、女性活躍的場域不同,不過如今看到沈恩的敘述,想起來確實在緬甸其他著名的觀光景點,小吃店、旅宿櫃檯、商店等反而是女性員工/店主更為常見。
至於美好的緬甸印象,「緬甸人實在親切極了,總是滿臉笑意,和藹可親」,對照著後來的宗教衝突,曾經友善、溫和的緬甸人,怎麼會無情、暴力對待羅興亞人呢?他認為是「軍方近年來系統的進行反羅興亞人的強力宣傳」,透過「運用有效的種族主義宣傳與強烈偏見,導致虐待與殺戮層出不窮」。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沒有牆的學校
從曼德勒回到達卡的沈恩,開始接受正式的學校教育,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也逼近南亞了。「在大戰期間,加爾各答與達卡總是經常防空警報大作,家家戶戶都要進行防空訓練。1942年12月,我們家和一些親朋好友在加爾各答過節,日軍就在一個星期內轟炸了碼頭區五次」。
因為日軍空襲的緣故,沈恩從達卡的學校轉到桑蒂尼蓋登。在這所「沒有牆的學校內」,除了雨天和實驗課程外,其他課程都是在戶外上課,因為「泰戈爾不想要讓我們學生的思想禁錮在自身族群裡——不管是宗教或其他任何類型的族群歸屬——也不想讓我們受自己民族所限(他對民族主義的批評可是不遺餘力呢)。儘管泰戈爾喜愛孟加拉語言和文學,但他十分厭惡囿於單一文學傳統,因為那不只會養出墨守成規的愛國主義,更是忽視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寶貴教訓」。
這所學校的核心,在於教會學生理性和自由的重要性,「一個人要擁有自由,就要有理性才能行使——即使什麼也不做也是在行使自由的一種表現」。
除了課程外,學生也能從造訪學校的貴賓學習不同的知識。其中一位訪校的特別貴賓,便是1942年2月訪問加爾各答的蔣介石,當時他對學生用中文演講一個半小時,不過學校並未安排翻譯,「所有學生一開始都十分專注聽講。不過沒多久,底下開始出現窸窸窣窣的雜音,後來大家更是似無忌憚的聊起天來了」。
學校安排幾位同學和貴賓喝茶,「我對蔣夫人的印象十分深刻,她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在眾人面前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樣。學校高層為了沒有提供即席翻譯向他們致歉,蔣夫人特別澄清蔣先生並未覺得不悅」。
幾年後的1945年12月,甘地也來校演講,「他很願意幫大家簽書,只要捐出五盧比——這真是舉世難見的收費標準——當作他推翻種姓制度的基金」。沈恩捐了五盧比,「他抬起頭來感謝我的捐獻,然後笑著對我說我抵抗種族制度的戰爭開始了」。
泰戈爾認為教育能促進經濟和社會的改變,他的願景也吸引了不少專家來任教,其中就包括了專精中、印歷史和佛學的譚雲山(1898-1983),他成立了中印文化研究中心,致力於中印交流。
他的子女們或在印度出生,或後來也移居印度,幾位之後也在印度的大學裡任教。他的三子譚立,是沈恩的好同學和好友,「我喜歡跟他們兄弟姐妹在一塊兒,經常在他們家一待就好幾個鐘頭。我也喜歡跟譚教授夫婦談話,這些對話彷彿為我開啟了一扇門,讓我能深入認識中國」。二人的友誼持續到2017年時,譚立過世為止。
另一個戰爭期間的重大事件,便是孟加拉經歷了大饑荒(Bengal famine of 1943),造成約三百萬人死亡,後來沈恩分析這此饑荒的原因,原來不在於糧食供給不足。
1942年時孟加拉的糧價開始飛漲,沒多久街上開始出現長期飢餓而精神錯亂的人,因為日軍逼近印緬邊界,在南亞大陸上的盟軍進駐、建造機場等軍事設施,這些戰備為當地帶來就業機會和薪水,軍事人員大量收購和消耗糧食,於是「龐大的需求帶動了物價上漲,而買賣糧食的市場操作與恐慌心態更增強了上漲的趨勢」,於是相對富裕的人還可以面對這種情況,可是薪水跟不上物價漲幅的鄉間的農民和勞工,他們逐漸失去購買糧食的能力,而這樣陷入挨餓情況的人越來越多,更不用說直到1943年10月,饑荒的消息都被刻意封鎖著。
宗教衝突、階級不平等和經濟學啟蒙
1944年時,一位在沈恩達卡的家附近工作的穆斯林男子被刺傷,他負傷到沈恩家中求救並討杯水喝,「當我試著撐起卡德爾血流不止的身子,好讓他能喝上一口水,聽著他愈來愈急促的呼吸,我突然看清了這種故意劃分族群和製造敵意會帶來什麼樣的野蠻行徑與恐怖後果」。
受傷的卡德爾雖然緊急送醫,但終究沒能活下來。他是因為生活、為了微薄的薪水,必須在這族群械鬥的動盪時刻,冒險到印度教徒的區域工作,不然自己的孩子就必須挨餓,而這也使得1940年代的宗教衝突中,印度教和穆斯林的民眾皆有死傷,「但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同一階級(來自勞工家庭和身無分文的貧民家庭)」。
那是動盪不安的時候,雖然之前大陸上各地偶有不同信仰導致的衝突,但是1940年代的衝突不同於以往,政治分離的想法有支持、也有反對者。「隨著饑荒和暴動出現在我們生活周遭,我發覺階級分析確實多少能幫助我們理解究竟是什麼使得我們要受苦受難,包括貧窮與不平等,還有被剝奪基本自由(包括不必冒著性命危險的自由)」。
事實上,宗教衝突的原因還包括了經濟不平等,1793年康華利法典頒布後,「規定地主向政府繳交的稅金永久不變」,大部分的地主是印度教徒,被剝削的佃農是穆斯林,這種田賦永定(Permanent Settlement)造成的不平等相當深遠,直到1947-48年間,這個制度才被取消。
後來成為沈恩同事的史學家古哈(Ramachandra Guha,即《印度:最大民主國家的榮耀與掙扎》),他第一本書的研究課題就是這個制度,也在序言中坦白自己就是這個制度的受惠者,而他探討的角度「不是以大英帝國如何剝削臣民並強調自身利益為焦點,而是聚焦在出於各種善意的思考最後怎麼會在孟加拉推出這麼一團東拼西湊的田賦政策——以及烏煙瘴氣的實施狀況」。
1951年沈恩即將開始大學課程,對社會不平等的關注(其實還因為同學博學多聞的兄長主修經濟學),讓沈恩在加爾各答的總統學院註冊了經濟學課程,因為經濟學可以涉及他從小以來就有興趣的數學和梵文,而且當時就有的想法:「要努力讓印度改頭換面——要打造出一個不像我們那時那麼貧窮、不平等、不正義的國家。而懂一點經濟學可能就是改造印度的關鍵」。
留學劍橋三一學院和多重身分
1953年的秋天,沈恩到了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深造,最不適應的地方是秋、冬季,太陽很早就下山,「怪不得英國當年會那麼執著於建立一個日不落帝國了」。他接觸到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有些好朋友是位置相近,有些人和我有同鄉之誼,有些人是在政治上志趣相投,有些人是彼此脾性相合,還有些人——像我在放射治療中心認識的這些醫生一樣——則是與我患難與共」。
在這段三一學院時光的交友圈,「回顧我在劍橋展開的新生活,我想不是只有強項才能教人惺惺相惜,脆弱之處也同樣能夠凝聚人心吧」。
經濟學的教授們也各有所長,不過沈恩一直對福祉經濟學很有興趣,因為「這一領域直接評估社會中個別成員的福祉,並加總衡量出社會整體的福祉」,只是好多位師長對這個方向沒有興趣,也覺得要繼續研究下去頗有難度,因此他只能在興趣和指導教授的建議稍稍妥協,以技術選擇(Choice of Techniques)為研究主題。
其中一位經濟學者斯拉法,在這個領域內「至少有三大觀念或見解來自斯拉法(Piero Sraffa, 1898-1983)的研究」,而他的哲學觀念還促使維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1889-1951)推翻自己早期的《邏輯哲學論》,即「試著脫離語言受到使用的社會情境來看待語言」,進而發展出《哲學探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的後期哲學思想,就是「改為強調為言說提供意義的習慣與規則」,維根斯坦曾說「斯拉法教會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人類學眼光來看待哲學問題」。
沈恩在與斯拉法飯後散步時,談論關於社會選擇的議題的啟發,也就是「勸說與論理在社會選擇中的重要性」,因為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發生時,英國本土因為戰時的準備和分配,反而避免了糧食不足的問題,期間英國政府是刻意封鎖饑荒的消息,直到吹哨者出現,西敏寺不得不面對、英屬印度政府不得不應對,因此壓制公眾輿論是不利於社會的。
沈恩認為:三一學院不僅是經濟學重鎮,更是各個領域人文薈萃的要地。這點又吸引了海內外的學生和學者前來,他們在此互相切磋、交流,激盪出更精彩的學術火花。
不僅如此,各個學者的多元背景,也讓人反思自己的多重身分,「總認為身分是一種獨特——而且明確——的階級區分機制的社會分析學家,忽略了我們每個人都具備著豐富的多重身分。我們的出身地緣、公民身分、居住地、語言、職業、宗教、政治傾向,以及其他不一而足的各種身分面向都能融洽的並存在我們身上,我們才因此是我們」。
小結:看世界的觀點
我很喜歡書封採用的照片,那是沈恩青少年時和妹妹、堂姐一起從窗戶向外望的照片,拍攝地點是桑蒂尼蓋登,他們眼前的是拍攝者和桑蒂尼蓋登的一景,這種意象就像是桑蒂尼蓋登在你眼前,但那其實也是世界的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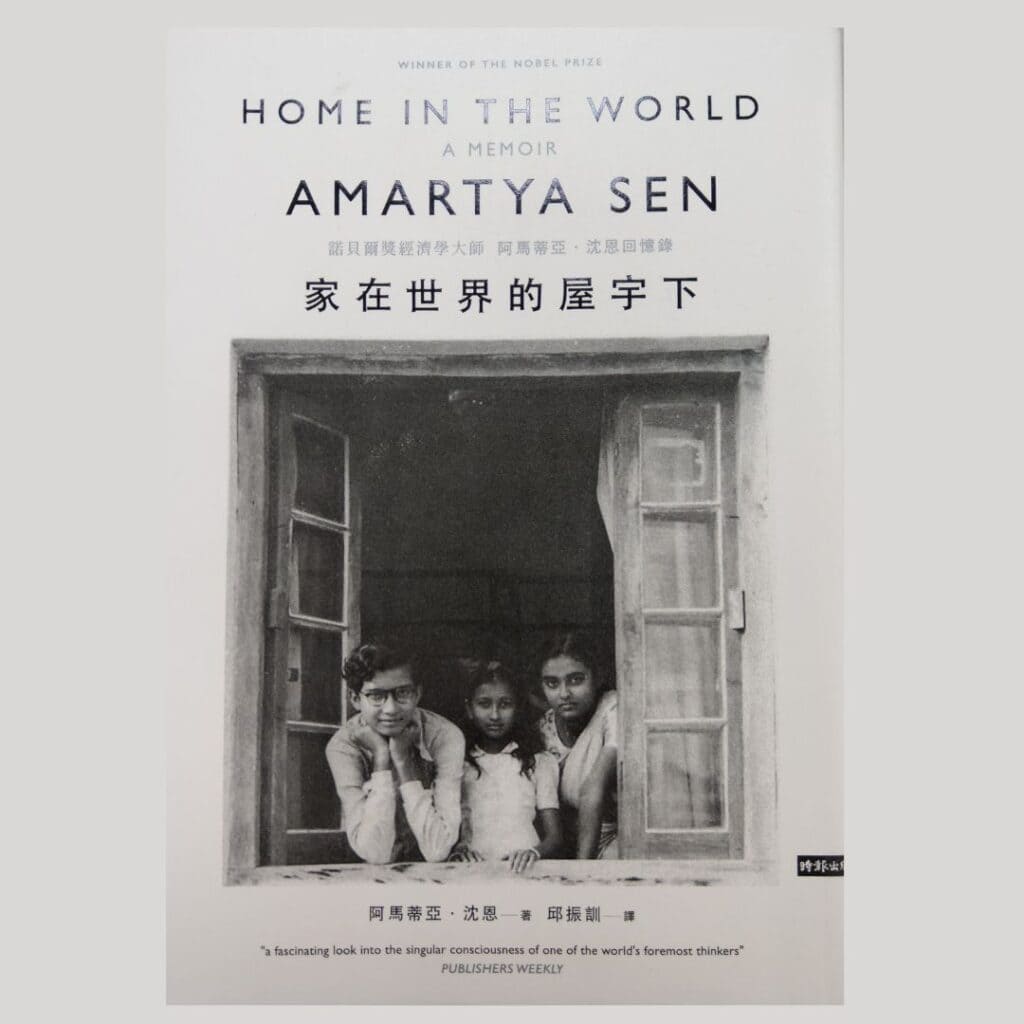
透過本書回顧沈恩的人生,雖然其實算是他前半生的回顧,時間軸大概到1960、70年代左右,不過理解到他看世界的觀點,都和他的童年、青年的成長經驗有關,並且影響他未來的學術關懷,而這又呼應了他對社會議題的關心。
「我認為要思考世上不同文明,共有兩條截然不同的進路。其中一條是採取碎片式觀點,把紛呈萬象都當作是不同文明的具體展現。這條路子認為不同碎片之間彼此敵對,近來可說是蔚為風潮,恐將延續文明衝突的看法。
另一條進路則是採包容式,專注在從各種不同展現裡找出最終那個文明──也許可以稱之為世界文明──開枝散葉的證據」。
沈恩對於世界的理解,傾向於包容式觀點,而那或許也是世界在邊際消除之後,展現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