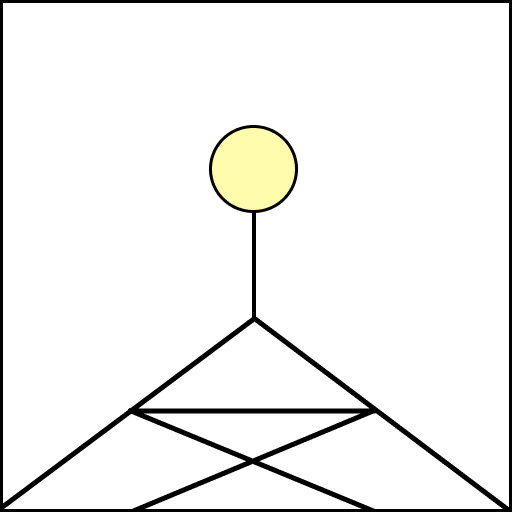讀《民族重建》,了解錯綜複雜的東歐史

冬天的立陶宛很孤寂,彷彿有一種流淌百年的孤寂感,走在又雨又雪又濕又冷的維爾紐斯(Vilnius)街頭,在並非觀光旺季的時候,久久都未必會與別人擦肩而過,所有的聲音也像是塵封在雪裡。
在波蘭東部有個盧布林(Lublin),這裡鄰近烏克蘭,街景乍看之下和華沙或其他歐洲城市沒有什麼不一樣,有著黃、藍、白、粉的房屋搭配紅瓦,還有行李箱輪子殺手石板路,但是附近有個惡名昭彰的Majdanek滅絕營。
這些是城市如今讓人看見的「現在」,不過錯綜複雜的過往則是在這些國家、城市成為這樣的稱呼以前,那也是民族重建的啟程。


從血色大地到民族重建
歷史學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的《民族重建:東歐國家克服歷史考驗的旅程(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Lithuania,Belarus, 1569-1999)》,探討了四百多年來的東歐,這個在16世紀為波蘭立陶宛聯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的區域,不僅幅員廣大、語言和族群多元,還產生歐洲的第一部憲法,然後在經歷了不同政權、強勢文化等多重影響下,如何分別成為了波蘭、立陶宛、烏克蘭和白俄羅斯?
在《血色大地》中,史奈德敘述了納粹德國和蘇聯於東歐地帶權力競逐時,輪番加諸於此地和當地人民的磨難。《民族重建》則將時序往前推進,從波立聯邦開始,以在此之後的民族概念演變為軸心,經歷了不同勢力角逐、衝突、瓜分、占領和族群清洗,新成立的民族國家試著化解宿怨、找出和平共存之道。
強勢的波蘭文化,促成了民族運動
「現代各個民族的概念,誕生於與過往敵人的密切互動」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這裡曾是「波蘭和猶太文明的中心」,甚至被稱為北方的耶路撒冷,這個立陶宛人口中的維爾紐斯,是波蘭人的維爾諾(Wilno)、白俄羅斯的維爾尼亞(Vil’nia)、猶太人的維爾內(Vilne),俄羅斯則依時序分別稱之為維諾(Vil’no)、維納(Vil’na)、維紐斯(Vil’nus)。
這些多元的稱呼反應了各方對此地的認同,進而演變出後來的民族運動。
至於波蘭文化的影響力,在這個在波立聯邦時期,甚至於是羅斯帝國時,在此帝國疆域內最廣泛流通的語言、文化,也在日後的現代民族主義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而「大公國貴族的傳統文化都以波蘭語和書面斯拉夫語記載」,精通波蘭語也代表了不同一般的社會階級。另一方面,說立陶宛語的農民受到宗教的影響,19世紀慢慢轉向白羅斯語,因此「斯拉夫語區的擴大,提供日後波蘭與俄羅斯文明同化的跳板」。
「如果我們將目光鎖定19世紀末歐洲的鏡子迷宮,就會看到民族概念以各種奇怪的角度被反射,各地的民族主義者駐足鏡前,看著他們眼裡獨特、純粹、美好的形象並沈醉其中」。
史奈德分析19世紀末的立陶宛民族運動,他們努力將立陶宛文化擺脫波蘭文化的影響,於是「立陶宛語其實是在一個德國人的建議下,採用捷克語的拼寫方案,最終在俄羅斯境內擺脫了波蘭語的影響」。
另一方面,烏克蘭民族運動者也接連經歷面臨波蘭、斯拉夫文化和政治勢力,這也使得波蘭對於烏克蘭民族想像的形成居於關鍵的地位。因此烏克蘭運動者不僅要面對如加利西亞90%高階行政官員皆是波蘭人的狀況,亦即「不只要對抗波蘭人掌控的政府,還要對抗整個波蘭民族運動,因為後者不但致力於打造波蘭人的公民社會,更打算將加利西亞建立成波蘭人的民族國家」。
隨著加利西亞的知識分子在1900年達成了「烏克蘭人應該在族群文化疆域上追求獨立」,於是「這些源自近世的社會、宗教和語言差異,如今都在運動者和教士手中重塑成現代民族主義的形貌」,當宗教、語言、文化與特定民族認同相連結,在此之後此地的波蘭語已失去原本的文化、階層的特殊地位,只是眾多語言的一支而已。
世界大戰加劇波蘭和烏克蘭的對立
在一戰結束的時候,烏克蘭民族運動者的目的是要在加利西亞建立民族國家,這與立陶宛人希望建立一個以維爾紐斯的獨立國家願景一樣,不過立陶宛在一戰各方勢力爭奪下,有幸生存了下來,但是烏克蘭人卻因為「地緣政治的價值」,即使奧匈帝國、帝俄相繼解體,各方對於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地區的處置沒有共識,也不認為烏克蘭有權繼承前帝國的土地,在這段期間,除了國家間的戰爭之外,還有無數的「國家內部的武裝衝突,以及各種游擊行動、土匪劫掠和大屠殺」,這些行動造成約一百萬名的烏克蘭居民傷亡。
這個區域在1921年後大部分被併入波蘭,剩餘區域則納入蘇聯,後者在史達林主政、經歷大清洗和大饑荒前,曾有一段短暫的協助建立烏克蘭文化的歲月,讓知識份子以母語創作,流通的報紙和書籍、學校教育也是烏克蘭語。至於在波蘭治下的烏克蘭民族運動者,他們認為「波蘭就是烏克蘭民族運動的最大敵人」,且「對波蘭的敵意也蓋過蘇聯政權引起的廣大爭議,許多烏克蘭民族運動者甚至把蘇聯當成幫助烏克蘭建國的盟友,因為它建立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二戰爆發之後,這個地區短期內數度易主,1931-44年間,「波蘭人和烏克蘭人不斷歷經各種戰爭、占領、饑荒、報復、驅逐和種族滅絕」,而戰爭帶來的雙重占領,也讓此處統治正當性的問題再次出現。納粹德國和蘇聯都曾施行各自的大規模族群清洗和種族滅絕計畫,為日後族群清洗,昔時政權的協作者成為日後衝突時,種族清洗的執行者。加上波、烏社會菁英和力量幾乎在戰爭中被摧毀殆盡,納粹政權分而治之的手段,都讓波蘭人和烏克蘭人的對立更為嚴重。
「族群清洗產生的其中一個惡果,在於它將某些特定的暴行貼上了特定民族的標籤。那些施行族群清洗的人,藉著民族大義謀殺個人與個性,不僅是在羞辱與激怒倖存之人,將這些倖存者推向民族主義,還讓自己的族群成員淪為民族復仇的靶子。」所以烏克蘭人對波蘭人的族群清洗,招致波蘭人的報復,這又成為烏方政治宣傳的工具。
一方的攻擊多野蠻殘暴,另一方的回擊必定也是冷酷無情。光在1943-44年的盧布林和熱舒夫(Rzeszow)地區,波、烏雙方共殺害彼此約五千名的居民。
種族清洗和強制遷移
二戰之後的史達林,對於波蘭、烏克蘭、白羅斯長期的民族問題,決定沿《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劃定的邊界推行族裔同質化政策,「將人口疏散或遣返至屬於他們的民族故土」,於是經歷了數次強制遣返的行動,大大改變了百年來猶太人、波蘭、烏克蘭等族群混居的狀態,這些地區也等同完成了族群單一化,雖然並不算非常徹底。
後來成為西烏克蘭的加利西亞,1939年有39萬波蘭人口,至1947年僅剩七千,約減少98%。沃里尼亞納入波蘭,當地戰前的烏克蘭人口是60萬左右,戰後僅剩三萬,減少了95%,而二地的猶太人口皆少了97、8%。
某方面來說,「民族認同絕不是由族裔決定的必然命運,而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下做出的政治抉擇」。
展望未來的外交政策,歷史就交給歷史學家處理
戰後的波蘭對東政策,結合了戰略擘畫者的所見和預見,成為了融合現實主義,支持東歐的共產國家進入國際體系,也主張立陶宛、烏克蘭和白羅斯應獨立,而它們的獨立能保障波蘭的安全、帶來實際利益。
1990年代時,相繼著德國統一和蘇聯解體,波蘭亦著重與東方的鄰國維持良好關係,採行對東的雙軌政策:一方面與莫斯科的蘇聯中央政府聯繫,以確保蘇軍徹出波蘭,另一方面則是與蘇聯的各個共和國聯絡,將之視為國際法主題,以便外交正常化,並一再重申波蘭不會向立陶宛和其他東邊鄰國要回戰後失土。
1992年的波蘭外交部長斯庫比謝夫斯基提出了歐洲標準,也就是為了解決歷史爭議,將參照具體的歐洲法律規範,彼時的德國和波蘭藉由這樣的標準處理鄰國關係,二者皆透過「以成為歐洲未來的一分子為號召,阻止20世紀的民族衝突再次發生」,此外,「在兩個的政策中,歐洲都提供了足以服人的理念和說法,使得參與的國家願意達成和解」。
後來,這樣的政策成為波蘭社會的常識,他們清楚認知「波蘭民族曾經失去領土是一回事,但波蘭當下的國家利益則是另一回事」。因此,「在兩個彼此承認與解決國界及少數民族問題後,再重回歷史討論,便能進一步加深兩個的和解」。
「把歷史留給歷史學家來處理」他們真的透過來自雙方、兩個非政府組織與兩所國立高等院校,共同規劃一系列研討會,並且在每個主題研討後,以二種語言發表聯合聲明,列出雙方的共識和歧見。
雖然結果並非人人滿意,但仍顯現出雙方共同面對過往的努力。
小結
首次接觸波立聯邦這個名詞,大概是幾年前我造訪立陶宛和波蘭的時候,試著了解波羅的海三國,但是當時只震撼於二戰時期德蘇勢力這對幾個國家的影響,並不清楚波立聯邦這段時期,代表著這幾個如今分別獨立的國家,曾經是多麼緊密,甚至於波蘭的文化和語言是曾在這個區域有著強勢的影響力,直到讀了《民族重建》,才知道東歐這塊土地上這段錯綜複雜的過往。
我們看到這些地方的現在,他們能成為如今的模樣,其實是經歷了長期的衝突、對立、死傷,然後在鐵幕揭開的同時,波蘭務實的展望未來、建立與鄰國的關係,才能避免因邊界爭議讓人民再次承受無情戰火。
這塊血色大地上的人民,遭遇的磨難已經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