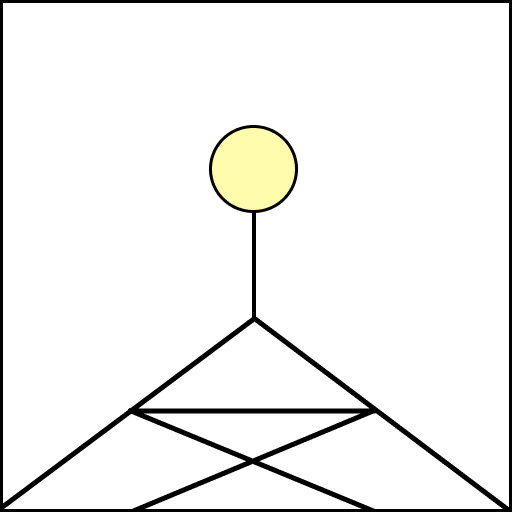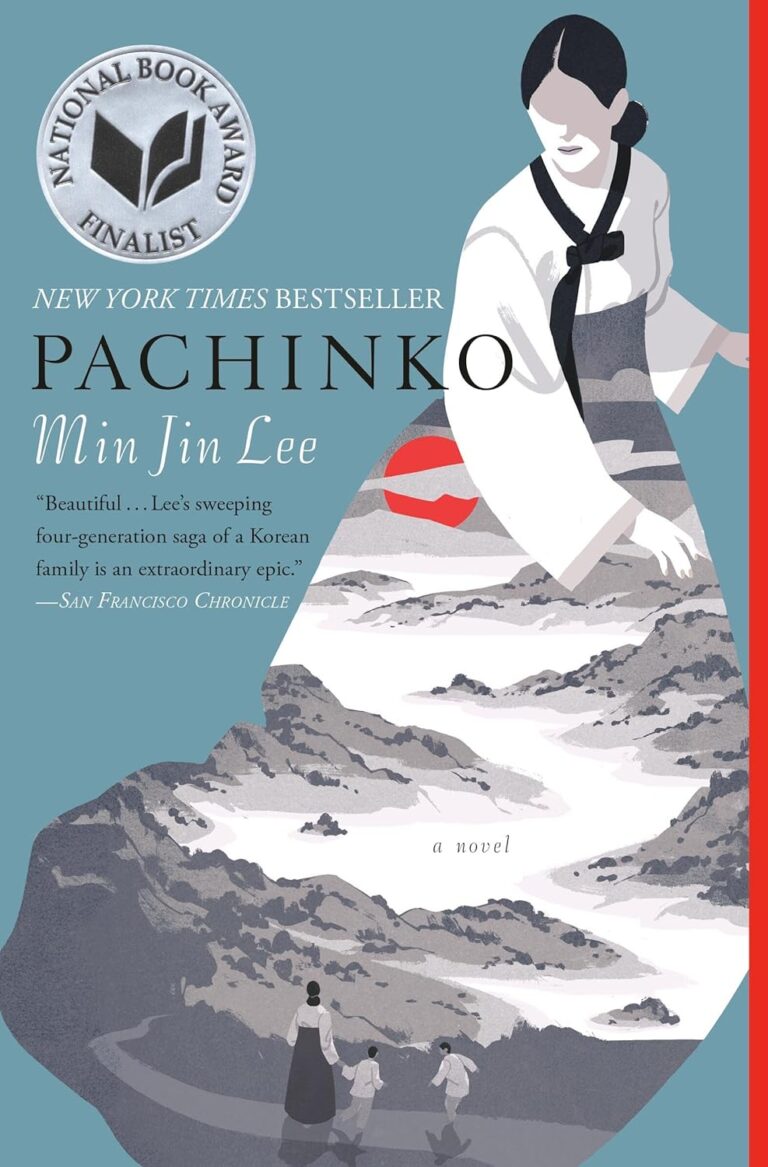德國如何面對《父輩的罪惡》

《父輩的罪惡》所探究的過往
2018年德國統一紀念日橫掛在布蘭登堡大門上的主視覺,是一群在圍牆上歡欣鼓舞的青年人們。不知道見證了那刻的人們如今在何方?那是個振奮人心的時刻,但是時光飛逝,要傳承給下一代的過往,究竟是怎麼樣的重擔。
蘇珊.奈門(Susan Neiman)著作的中譯名《父輩的罪惡:德國如何面對歷史,走向未來?》(Learning from the German: Race and the Memory of Evil),讓我聯想到了近十年前的德語影集《我們的父輩(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這是一部以二戰為背景的劇集,透過五個角色在戰爭中不同的際遇,帶出戰爭各個面相,無論是士兵、護士、猶太人……戰爭幾乎徹底改變了每個人。這部劇呈現了德國對戰爭的反思。距離二戰結束已將近八十年,對於200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而言,那場戰爭乍看已非常遙遠,但是它留下的痕跡卻彷彿是無所不在。
這一條釐清過往的道路並不輕鬆。雖然東德人一直稱這天為解放日,但西德是直到1985年,西德總統魏茨澤克發表了那場著名的演說,將二戰結束的日子稱為解放日,而在那之前,德國民眾對戰爭結束是抱著矛盾的心情。
德國如何面對這段過往,則是作者在《父輩的罪惡》所探討的,並對照美國南方對於南北戰爭的態度,其存在至今的種族主義。作者對照二處面對過往的不同態度,以使讀者更為了解今日的情勢。
如作者所言,雖然德國的釐清過往至今仍不算成功,不過值得借鏡之處在於:「戰後德國經驗中的機制與錯誤構成了一個緩慢而有缺陷的過程,映照著美國朝著正義與和解所邁出的猶豫步伐」。
二戰後的德國和南北戰爭後的美國
作者認為,「與其關注二處的細微差異,不如盡量利用能在其中學到的事情」。
作者在德國的經歷,最吃驚的發現莫過於大多數德國人都曾把自己的痛苦置於一切之上。他們基於各種緣由,對那段過往沉默不語。直到68世代打破了沉默。他們的父輩,便是生活於納粹時代的人們,隨著越來越多關於戰爭責任的審判出現,他們理解到:父母無法哀悼、無法承認責任,甚至無法談論戰爭,不幸的子女就得肩負表達之責。
另一方面,本書作者透過東、西德一些數據的比較,呈現兩德對於那場戰爭的不盡相同態度,甚至當西德政府仍還有許多前納粹任職的時候,東德一開始即不遺餘力的清除過往國家社會主義的痕跡,中學教育上也有相當比例有關大屠殺的德語文學。此外,面積比東柏林大概多70平方公里的西柏林,政府設立約177個國家社會主義受害者紀念碑,東柏林則有246個;若以受害者賠償金總額保守估計,西德賠款金額約為195億馬克,東德為900億馬克,東德人口為西德的四成,因此人均賠款額比例約為110:3。
不過,作者亦觀察到東西德雙方不同的立場,前者反法西斯、後者反共,因此東德認為:作為德國土地上第一個反法西斯國家,我們已切斷今日與法西斯歷史間的一切連續性;西德則是:作為壓制個人自遊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共產主義並不比法西斯主義更好,因此東德根本沒有切斷與昨日的連結。於是在冷戰的氛圍下,「人民往往只能沉默以對」。
若對美國歷史只有概略的了解,並不清楚南北戰爭的結束,不代表奴隸制的消失,反而是透過如吉姆.克勞法案,落實了種族隔離制度。本書作者在密西西比與相關人物的談話,以此處來檢視美國的傷痕。選擇此處,是因為「在密西西比遭私刑處決的人數比在全國任何地方都多」。
借鏡德國面對過往的方式
「如果你要紀念大規模的罪行,你得非常、非常小心,不要讓其變成審美行為」。
作者主張借鏡德國,因為「德國釐清過往的嘗試相當緩慢、不情願而不完整」,但是因為德國面對過往,也徹底改變國家的形象:從自視可憐的受害者變成自視為有責的加害者。
總而言之,若當下是塊千片的拼圖,將之放大檢視,每一塊拼圖便代表著不同的過往,而過往的點點滴滴便是如此形塑出當代的模樣。因此,未來要成為什麼模樣、過往如何詮釋,取決於現在面對過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