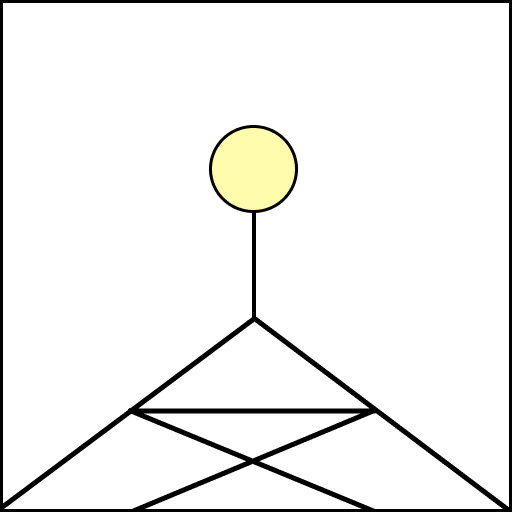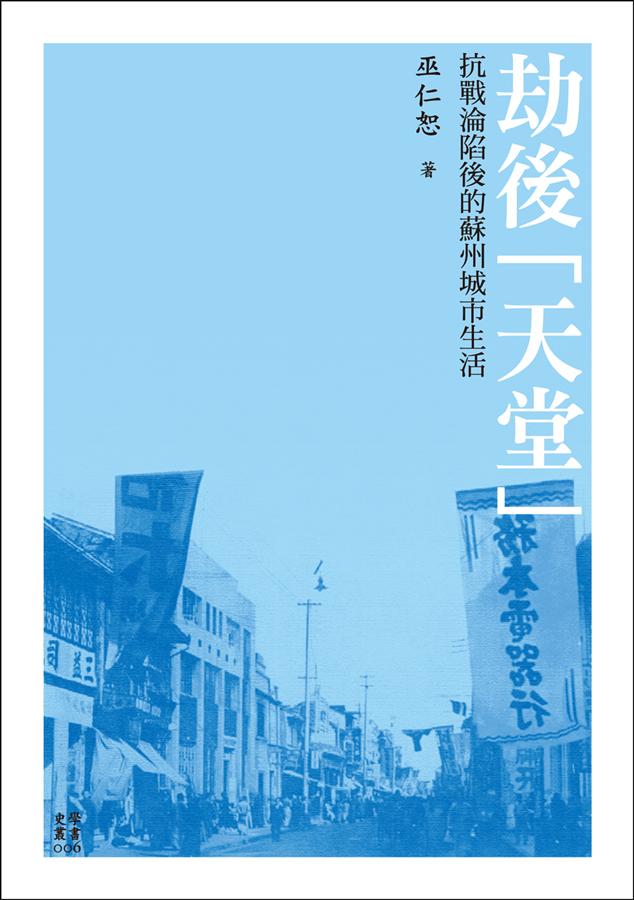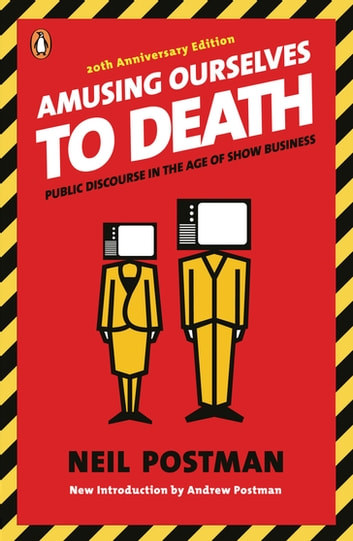車諾比核災真相:《車諾比的聲音》道出500位親歷者的生命證言
車諾比的悲鳴,淚慟交織的生命證言

2022年2月底開始的戰爭,讓烏克蘭成為國際注目的焦點,而戰火下車諾比核電廠的狀況亦是備受矚目,並且讓人想起發生在30多年前的事件:車諾比核災,這個被紀錄在歷史課本上的重大核災事件,後來的我們都知道了核輻射的恐怖,也多少聽過車諾比核災之後,這個區域已經不適合人居了。
在核災事故的前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或著,若傾聽車諾比的聲音,會訴說著什麼故事?
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亞利塞維奇(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訪談了無數經歷車諾比核災的人員,包括當時的居民、善後人員或其遺孀、鄰近區域地方首長、核子研究所人員,以及之後進入限制區居住的人們……完成了這本《車諾比的聲音:來自二十世紀最大災難的見證》,由不同的經歷還原事發後的景況,那是淚慟交織的生命證言。
和平核電與死亡輻射
時間回到1986年4月26日的凌晨時分,車諾比核電廠的反應爐起火了,第一批趕到現場的消防員以為只是發生了一般火災,沒有什麼特別的,大部分的人也是這麼認為,畢竟只有軍事核武會造成傷害,和平核電不會,因為在1980年代,「核電廠是未來的象徵」,它代表著未來,也象徵著幸福的社會。
所以在核災發生的當下,在那個週五到週六的深夜,居住在距離反應爐三公里處的居民,他們在幾乎是在第一線的位置看到反應爐的狀況,「回想起來那道豔紅的火光仍歷歷在目。反應爐內部發出光芒,顏色相當不可思議,與其說是普通的火警,倒不如說是場精采奪目的光影秀」。
大家觀賞著這前所未見的奇景,沒有人想到,所謂和平核電也會對人類造成毀滅性的影響,死亡其實也是如影隨形。
核災是另一種形式的戰場,返家才是不幸的開始
這是戰爭嗎?好像這個情況和戰爭沒有太大不同,「城市上空有直升機盤旋,街道上有軍車來來往往噴灑某種泡沫,男的都被抓去當半年兵,就像打仗一樣」,居民被通知撤離,不過政府承諾三天後就能返家,於是他們只能匆促離開,留下了溫暖的家園、熟悉的街道、結實累累的果樹、花團錦簇的花園,還有不被允許帶走的寵物。
對於經歷過阿富汗戰爭的軍人而言:「我知道從戰場回到家代表死亡的威脅已經過去,車諾比核災的情況卻完全相反,人反而是到了家才一個個死去。回家才是不幸的開始…」
大量的人員被送去執行善後任務,清理核電廠、被汙染的土地、物產和寵物,但沒有足夠的防護裝備。「只因為是軍事命令」,許多人被丟入充滿輻射的環境,機器人承受不了輻射一個個燒壞了,現場的清理只能仰賴穿著橡膠衣和手套的士兵。
「需要的應該是專家,不是人肉砲灰」,參與善後工作的人付出了生命和健康的代價。
「從軍中除役之後,政府簡單頒發一紙獎狀和一百盧布的獎金,而他們就此從我們國家這片廣袤的土地上銷聲匿跡」。核災之後的真相,一個個參與第一線救災的人接連倒下。
官方三緘其口,放射積雲下人民日常
「一切都很好,情況全在掌控之中」這是沉寂多日後,5月1日時戈巴契夫公開傳達的訊息。
對人民而言,「政府避而不談,醫生也三緘其口,我們什麼答案都得不到」輻射其實無所不在,但沒有人清楚真實數值,含輻射量的物產在市面流通,「其實不光政府欺騙我們,連我們自己的潛意識也在自欺欺人…」因為作物長得那麼好,怎麼會不能吃呢;軍隊都出動了,一切情況應該是可控的。
在那個時代背景之下,對政府高層而言,避免地方的恐慌是首要之務,而且初期沒有人能完全明白這場意外的規模有多巨大,事發之後輻射物質也因為風向的關係被吹往世界各地,其中白俄羅斯受到的影響最深,不知情的人們就是在放射性積雲下,繼續著日常生活,受到污染的土地生產著作物、畜養動物,被不知道確切情況的人民食用。
我者和他者:災後的車諾比移民
事件之後,切身經歷讓他們的感受是人被區分成兩種:我們車諾比災民和你們其他人。所以有些人選擇返鄉,因為如果離開管制區生活,「車諾比移民」就必須面對他人的異樣眼光,但是留在當地大家都是受害者,彼此不會對彼此戒慎恐懼;不然就是蘇聯境內經歷內戰的人們,到了這塊無主之地,沒有什麼好怕的,「只有人會讓我害怕,尤其是拿槍的人」
歷史的波瀾壯闊,相對著人的微不足道,比起心羨著創造歷史、參與歷史事件的人們,經歷著這個事件的人們:「我不想背負歷史的重擔活在一個意義非凡的年代,渺小的我承受不起,因為重大的歷史事件往前推進時,才不會注意到我,只會把我踐踏在腳底下」。因為被紀得的只會是車諾比核災這一個事件,而忽略事件背後受影響的人,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獨特的,都有著獨一無二的美好。
傾聽車諾比的聲音,或許當時發生的一切不過是不同樣貌的戰爭,而戰火仍持續著,以有形、無形的方式,繼續影響著人類。